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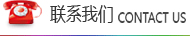
最近,在日本出現了一宗網上誹謗案例,日本的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在判案時產生了很大的分歧,地方法院認定無罪,而高院則認為有罪。這種分歧和沖突說明,直接引用現有法律管理互聯網,已經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問題,不進行專門立法,矛盾將越來越深。
被告的日本男子在自己的主頁上中傷一家餐飲店企業,稱其為“邪教集團”。東京地方法院在一審判決中認為,在互聯網上個人用戶傳播的信息可靠性一般較低,因此采用了較以往寬松的尺度宣判無罪。然而東京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則推翻了這一判決,判被告男子誹謗罪。日本最高法院認為,互聯網上發布言論的適用條款與出版物以及廣播媒體同等嚴格。該判決向人們傳遞了這樣的信息,即互聯網要遵守以法律為基礎的同樣的社會規范。
如果這個說法成立,是否可以依照現有法律來判斷所有互聯網行為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比如,上述判例的一個主要爭議就在于,在個人主頁或個人博客等地方發表的言論,是否能等同于傳統出版物。東京地方法院傾向于有所區別,而最高法院則認為毫無區別,顯然,網民對此也會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那么,如果缺乏針對互聯網應用的專門法律,就會出現上述對適用法律截然不同的理解。
上述這種行為還相對比較好做判斷,因為現實中也存在誹謗行為。但有些互聯網應用方式則很難找到完全對應的現實行為。碰到這種情況,就無法以現有法律適用來做判斷。比如,網絡游戲中有一類被稱為“打錢民工”的玩家,他們依靠熟練技術并花費大量時間獲得游戲道具和裝備,目的是將這些裝備道具出售給其他玩家以牟取現實利益。結果,這類行為因為威脅到廠商利益,而經常被廠商沒收裝備道具,甚至被封號。究竟是“打錢民工”違法還是廠商剝奪他們的權益,現實中很難找到類似行為進行對比。
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比如,現實中把自己購買的音樂碟借給朋友聽是合法行為,但如果復制出售并獲利,則侵犯了著作權人的知識產權。在某些社交類網站上,有很多所謂興趣小組,互相推薦、交流他人作品,如果內容足夠豐富、時效強、權威性強,則會有很多網民加入小組或經常瀏覽。即便這類興趣小組自身并未實際獲利,但其寄身的網站因為這類小組很活躍、點擊率很高,就可能獲得廣告商的青睞,從而獲得現實利益。當下,搜索引擎、下載類網站比較多地采取向著作權人支付版稅的做法,來解決矛盾,但這個規矩是否適用于社交類網站,則不好判斷。畢竟,興趣小組的行為更類似于現實中把自己購買的音樂碟借給同樣有興趣的朋友。
通過這些的舉例,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說“互聯網要遵守以法律為基礎的同樣的社會規范”這樣的話沒有問題,但當互聯網應用在現實社會里找不出對應行為時,以上說法可能落空。事實上,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的改變,必然改變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或者說,會創造新型社會關系,法律作為調節各種社會關系的準則,如果不能與時俱進,則必然無法與新型社會關系的需求相吻合。
互聯網立法的一個難點在于,社會對這個產業的研究遠遠不足,其自身日新月異的變化,也令管理者、立法者眼花繚亂、應接不暇。另外,立法所需要的知識儲備、專業儲備不足。以今年“兩會”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構成看,沒有一個國內互聯網產業權威人士,某些明顯對產業缺乏認識者的提案,往往被網民嘲笑,當作外行亂說話。所以,從路徑上看,加強互聯網管理的前提是促進互聯網立法,而立法的前提是做好知識等充足準備,需要產業界人士盡快進入這個程序。

